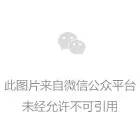发布时间:2020-08-17 11:44
大学的最后一个暑假,我有幸得到学院安排的香港实习机会,在香港有线电视新闻中心展开了将近两个月的实习生活。在有线新闻中心七个礼拜的实习分为两部分,前四个礼拜在港闻部,每天的工作是在正职记者的带领下,在香港各处跑新闻,现场采访报道;后面三个礼拜在节目部,参与一档周播时事清谈节目的策划制作。以前我来过两次香港,对这座繁华大都市还停留在剁手买买买的印象上。这段实习经历,不仅让我得以提升专业技能,更让我对香港媒体运作生态甚至整个香港的环境都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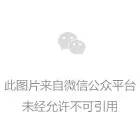
胡晓菁在香港实习。(胡晓菁提供)
香港没有独家新闻?
初到港闻部,我就发现一个现象:每次我们根据assignment去到指定的现场,都可以发现大量的媒体同行。一是因为大型的event主办方都会通知传媒到现场采访,二是因为各大媒体间的讯息是互通的,一“有料到”,行家之间就会通报资讯。除此之外,各媒体的采访对象也是一样,十几个麦克风,十几台摄像机对着同一个受访者。相差无几的画面,一样的受访者和同期声。这不免让我产生疑问,难道香港没有独家新闻吗?报道出来真的不会很雷同吗?因为在我想象中,记者应该是靠自己的慧眼挖掘新闻,不是这样有着满满的“套路”。
后来在深入了解和观察之后,我得到了答案。在香港这个不大但信息透明、聚集了有线、TVB、明报、苹果日报等十几家媒体的地方,的确很难挖掘到独家新闻。媒体要在激烈的竞争中争取到更多的观众,要靠独特的报道角度。即使是同样一段同期声,选取不同的侧重点,与不同的议题结合,也会组合成一条独一无二的新闻。举个例子,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在一次活动结束后接受传媒采访,就旺角骚乱后警队检讨、警方错将智障汉当成杀人犯拘捕、铜锣湾书店事件给出了警务处的立场。现场媒体会根据他讲的内容,评估新闻价值,选出一方面的内容与有关议题结合起来,做出很可能完全不同的新闻报道。反之,找不到一点趣味性和独特性的新闻,毫无疑问就会被kill掉。比如有线在香港动漫节派了两队crew去采访报道,其中负责采访排队市民的一队,就因为太general没有特别之处而被kill掉,即使动漫节是颇为重要的活动。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作为记者,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是必备的生存技能。在跑港闻的时候,我有好几次的任务都是去法院听审。受到媒体青睐的案子,通常都涉及到公众人物或者造成极大社会影响,公众会密切留意案情的走向。到法院采访的记者,就一定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收集信息。眼观六路,要在法庭上短时间内准确辨认出裁判官以及控辩双方的长相,尤其要记住被告人的外貌、衣着特征,在听完court之后要及时与在法院门外守候的摄像沟通,协助摄像辨认出被告人,拍到相应的素材(摄像不能进到法庭内拍摄,只能守候在法庭外,待法庭内的人走出来时进行拍摄)。在刑事案件提堂的court里,还要仔细看官方提供的控罪清单,清楚知道每一条控罪,不能有一点差错。耳听八方,一方面要认真听控辩双方的辩词和证据,以及裁判官的判词,另一方面在结束之后也要积极听同行的讨论,资源共享,查漏补缺,确认是否有遗漏或者错误的信息点,以保证报道的准确性。起初,对于还是菜鸟记者的我来说法庭采访确实有一定难度。去听旺角骚乱案件提堂的时候,被告人有十名之多,每个人的身材长相衣着相差甚远,我险些将他们几个弄混。而且当时的裁判官是外籍人士,全英发言,大量的法律术语听得我一头雾水。翻译只负责翻译重要内容给被告人听,在媒体席的我完全听不到。不过,这些问题,只能在庭下与同行讨论的时候来解决。当然,这样也存在一个风险,万一其他同行搞错了,大家就全部错了。
“能用一个字表达就不要两个字”
“简洁”、“通俗”是电视新闻稿的特点。写稿子时,能多简洁就多简洁,可以用一个字表达就不要用两个字。我对这一点感受颇深。指导老师在实习开始前就鼓励我们要自己尝试写稿,再对照出街的版本修改或者请正职记者修改。所以我有机会就会尝试写稿。记得那次,我在现场就把稿子写完,自我感觉良好拿去给带我的记者修改。没想到,短短几十字的稿,被她挑出了五六处写得不好的地方。她直指我的表述不够简洁:“提出担保申请”要改成“申请担保”,“对邮件内容进行审查”要改成“审查邮件内容”……都是诸如此类的问题,套用最直接的动宾结构即可。我才意识到,写电视新闻稿,不仅仅是表述清楚这么简单,还要表述简洁。不需要有什么文采,读起来、听起来顺口更加重要。短短几十秒的新闻里,要用最少的字,传递最多的资讯。
选题会必备research和brainstorm
与港闻组相比,在节目组的三个礼拜,体验和收获完全不同。这档时事清谈节目,主要形式是三位立场不同的嘉宾在两位主持的引导下就当下某一时事热点进行激烈讨论。节目组每周要负责确定选题、拍摄介绍短片、街访市民、联系嘉宾、收集观众意见等工作。当中,确定选题环节最为有趣,也最具挑战性。记得第一次被临时叫去开选题会的时候,我听着同事们噼里啪啦地抛出一个又一个选题,自己想要插两句话,又因为对香港情况不熟悉怕说多错多,就索性不发言了。更糗的是,选题会上会讨论适合上节目的嘉宾,本地的同事总可以轻松报出一串名字,我却要在一旁默默拿起手机,google一下他们讲的人是谁……有了前车之鉴,我下决心要好好准备剩下几次选题会,再也不能傻傻地只听不说了。然后便开启了疯狂的research模式:各大媒体的新闻网站、Facebook话题、相关论文、相关民调……搜索出海量的信息,再归纳整理出一个选题报告。一整天下来盯着电脑屏幕眼睛都花了。很辛苦,但我觉得research对于挖掘选题十分重要:看新闻、看facebook,我可以了解香港的hot issue,也可以知道港人关注和争论什么话题;看民调和论文,我可以进一步了解相关话题的研究进度,熟悉香港情况。事实证明这是有成效的。适逢立法会选举,又爆出两家媒体停止播放滚动民调的新闻,我提出了“民调误导选民?”的选题,主要针对民调的一系列争论,想探讨民调的权威性和可信性,尤其是在今年政党碎片化的形势之下。这个选题,得到了正职同事的表扬。另外,和同事们brainstorm也是挖掘灵感的好方法。在选题会上,每个人可以相互交流意见,往往可以碰撞出思维的火花,发掘到不一样的角度。有一次我提出了“传统媒体已死?”的选题,原本是探讨原因,可能会比较枯燥。同事们你一言我一语给出了自己的意见,举出电视盒子和数码广播的例子,说明政策方面对传统媒体并没有实施保护。因此,整个讨论的角度可以转变为政策扶持不足以及改进的方向。所以有时候,research是不够的,多和别人交流,说不定会有意外的发现。境外实习,学习为主,工作为辅。困难很多,但也一步步走过来了。对我来说,这段经历弥足珍贵,有成果,有错误,有友谊,有温暖的回忆。我最大的体会,便是知道自己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成长,需要进步。